鄂尔多斯文化——歌舞卷(六)
【漫瀚调】漫瀚调的起源与形式
漫瀚调产生于蒙古族、汉族杂居的人口较为稀少、居住较为分散的鄂尔多斯半农半牧区,发源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流传于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漫瀚调产生于近现代,是鄂尔多斯蒙古族音乐与晋西北、陕北汉族的民间音乐文化交流融合而产生的民间艺术,是以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中的短调为母曲,吸收晋西北汉族爬山调和陕北信天游的一些旋法和润腔而形成的新的民歌歌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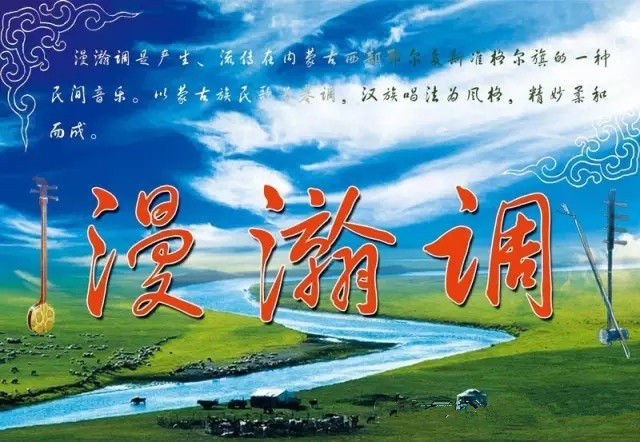
历史上,鄂尔多斯地区有过多种名称,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胡地”,秦汉时期被称为“新秦中”,“河南地”,唐宋时期被称为“河西”,明代初期被称为“河套”。15世纪中叶的明代天顺年间,蒙古族守护其圣主成吉思汗陵寝八白宫的鄂尔多斯部人驻河套地区,并一直在此定居下来,河套地区渐被称为鄂尔多斯。蒙古族鄂尔多斯部及蒙古族“黄金家族”入驻鄂尔多斯地区后,不仅把蒙古族文化的精华带到了鄂尔多斯,同时,由于成吉思汗八白宫设在鄂尔多斯,也使鄂尔多斯成为了蒙古族的精神圣地。
明代至清代中期,明清统治者为了削弱蒙古族力量,对鄂尔多斯蒙古族实行了隔离政策,限制鄂尔多斯蒙古族与中原汉族来往, 当时在鄂尔多斯南部,边沿设置了宽约5千米、长约数千米的隔离带,即“黑界地”,明令禁止晋、陕汉民越过黑界地进入鄂尔多斯地区进行农耕,也不准鄂尔多斯蒙古族越过黑界地计入晋、陕地区游牧。这一时期的隔离政策使鄂尔多斯地区处于封闭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使鄂尔多斯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收到了限制,另一方面也使鄂尔多斯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延续。
从15世纪中叶至新中国建立前,鄂尔多斯蒙古族一直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过着游牧生活。由于鄂尔多斯地域辽阔,人口稀少,牧民居住分散,自然环境恶劣,鄂尔多斯蒙古族形成了豪放、淳朴的性格和能歌善舞的生活习性。在蓝天白云下,辽阔的草原上,孤独的牧羊人为排解寂寞时而高长低吟。偶尔有客人到来,自然感到十分稀罕亲切,总要热情招待,“言不足以歌之,歌不足以舞之”。人人如此,家家如此,鄂尔多斯便成为名副其实的“歌海舞乡”。
明代中期至清代前期,鄂尔多斯地区的居民绝大多数为蒙古族,只有为数很少的汉民。蒙古族经营着单一的畜牧业,过着游牧生活。清代初期,有少量晋西北和陕北汉族农民逐渐进入鄂尔多斯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据陶克涛所著的《内蒙古发展概述》记载,“清朝,汉人往蒙古地方耕种土地,乾隆以前虽不积极奖励,亦未严加禁止。内蒙古上层阶级亦因租利而争招汉人或出典土地于汉人。”因此,晋西北、陕北地区汉族农民进入鄂尔多斯地区从事农耕的人数逐年有所增加。
嘉庆、道光以后一度实行“借地养民”政策,鄂尔多斯与晋西北、陕北接壤,加之鄂尔多斯蒙古族王公贪图租利,致使晋西北、陕北农民进入鄂尔多斯地区从事农耕的人数大量增加,鄂尔多斯逐渐成为蒙汉杂居、农牧业兼营地区。至光绪年间,鄂尔多斯的汉户与蒙户数量相等。晚清时期,清廷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了争敛地方钱财,在蒙古地区实行“放垦”正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认命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让垦务局大办垦务。这样,晋西北与陕北农民进入鄂尔多斯地区耕种土地,由私放私垦变为官办,成为合法化。鄂尔多斯地区与晋陕相邻,“放首当其冲垦”。大规模、合法化的放垦,使更多的晋陕农民进入鄂尔多斯地区从事农耕,于是鄂尔多斯许多地方逐渐成为半农半牧区。
清代前期,晋陕汉族农民逐渐进入鄂尔多斯从事农耕,主要以“租耕”、“伙盘”的方式进行,即民间所说的“跑青牛犋,春来秋归”。春天,晋陕汉族农民带着籽种、耕牛、农具,来到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租赁一片土地,在租赁的土地福晋搭起临时起火做饭的灶房,即“伙盘”,秋天,带着收获的粮食再回到老家山西、陕西。清代中期以后,一些晋陕农民、商人渐渐以长久性租用土地或购买土地的方式获得了耕地的长久性使用权,逐步在鄂尔多斯地区建盖房舍定居下来。道光年间以后,在鄂尔多斯定居下来的晋、陕农民和商人越来越多,至光绪放垦时期,形成了移民高潮。
晋陕汉民大量迁入鄂尔多斯地区定居后,既把晋、陕农耕文化和民间艺术带到了鄂尔多斯,同时也接受着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及蒙古族民间艺术的熏陶和感染。于是,晋西北、陕北的汉族民间文化与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文化在鄂尔多斯得到了迅速、充分的交流和融合。
大量晋陕汉民迁入鄂尔多斯地区后,使鄂尔多斯地区的经济结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人口分布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地区由牧区变为半农半牧区,有的地区完全成为农业区;许多草场、树林被垦伐为农田,也导致了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人口成倍增加,蒙汉族居民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统计,至1947年,鄂尔多斯人口数为38.23万人,其中汉族人口33.46万人,占总人口数的88%以上。
能歌善舞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常在劳作之余、喜庆之日以及待客之时演唱民歌。演唱时,有民间乐队伴奏,家里男女老少都唱,同时招呼邻居唱,邀请客人唱,这种红火场面,常常通宵达旦。这种民歌演唱活动叫“坐唱”。晋陕民间也有一种民间文艺活动叫“打坐腔”,是由民间乐队伴奏演唱二人台、山曲儿。鄂尔多斯蒙古族的坐唱与晋陕汉族的打坐腔形式十分相似,伴奏所用的民间乐器也基本相同,晋陕汉族迁居鄂尔多斯后,很自然地把打坐腔与坐唱结合到了一起。
热情好客的鄂尔多斯蒙古族人民每逢家里坐唱,都会邀请邻近的汉族人前来唱歌。迁居来的汉族人民与共同生活、劳动在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人民和睦相处、杂居交往,使蒙汉两族民间音乐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交流、融合和升华。优美动听、情感炽烈的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收到了汉族群众的喜爱。从晋陕迁来的汉族人在学唱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时,很自然地融入了一些晋西北、陕北民歌的润腔和旋法,使蒙古族短调民歌的韵味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汉族移民以对唱的形式,用爬山调、信天游的汉语歌词填唱的蒙古族短调民歌,使短调民歌在乐曲结构、速度、演唱方式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经过不断地学习、演唱和演变,就形成了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为母曲,融入晋西北、陕北民歌的某些润腔和旋法,在乐曲结构、旋律韵味、演唱方式方面既不同于晋西北民歌,也有别于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的一种新的民歌种类——漫瀚调。

漫瀚调的产生和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蒙汉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准格尔旗布尔陶亥乡60多岁的蒙古族歌手奇昆山为采访者演唱了一首父辈口里传下来的漫瀚调,从这首歌的歌词中可以体现出漫瀚调的产生和形成过程。其歌词如下:
毛日牙乌奎(马儿不走)拿上鞭子打,
努胡日依日奎(朋友不来)捎给一句话。
爬场毛驴也是依勒吉挖哇(毛驴哇),
小脚脚女人也是努呼日挖(朋友哇)。
这是早期的漫瀚调歌词,蒙语、汉语混用,每句歌词一半是蒙语一半是汉语,既反映了当时生活在一起的蒙、汉两族居民语言还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也反映出了蒙汉人民互相亲近,音乐文化相互接纳、相互融合的情况。

漫瀚调伴随着晋西北、陕北农民移居鄂尔多斯地区的过程而形成。从清代中后期晋西北、陕北汉民进入鄂尔多斯的过程和程度分析,漫瀚调的产生和发展至今已有150~200年时间。
漫瀚调的发源地,更具体的说是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证实这一点。
(一)准格尔旗位于鄂尔多斯东南部,直接与山西省偏关县、河曲县,陕西省府谷县相邻。准格尔旗马栅、魏家岇、长滩三个村(原为乡)在1950年前原为山西省河曲县辖区。准格尔旗的乡村有许多地名叫“伙盘”、“伙壕”等,这是晋陕农民初期进入鄂尔多斯并且临时设灶、春来秋去而形成的地名。至新中国成立前,准格尔旗几乎全部被开垦为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准格尔旗原来的28个乡镇中,只有一个纯牧业乡。
(二)漫瀚调的许多曲名为准格尔旗的地名、人名或发生在准格尔旗的故事,如《双山梁》、《德胜西》、《巨合滩》、《黑岱沟》、《白大路》、《二少爷招兵》、《妖精太太》等等。
(三)漫瀚调在准格尔旗地区流行最早,传播最为广泛。在准格尔旗地区几乎人人都会唱漫瀚调,人人喜欢漫瀚调,准格尔旗的民间歌手最早引起文艺界和学术界对漫瀚调的注目。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鄂尔多斯地区的文艺工作者柳谦、赵星、张玉林、张发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专家所发现、采录、整理的漫瀚调曲目,均来自准格尔旗的民间歌手。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得知,漫瀚调是蒙汉两个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漫瀚调产生于清代后期,至今经过了150~200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漫瀚调产生于蒙汉杂居、半农半牧、人口既不稠密,也不十分分散的地区,发源于鄂尔多斯准格尔旗。
来源:鄂尔多斯市群众艺术馆

